剧情简介
烦人的爱主要讲述了中年女性阿黛拉与母亲玛丽亚的纠葛展开。玛丽亚以“为你好”之名,控制阿黛拉的婚姻、事业乃至生育选择,甚至偷看女儿日记,干涉其同性恋情。阿黛拉表面顺从,内心却因压抑滋生出扭曲的恨意。
三角关系的崩塌
情人的背叛:阿黛拉的伴侣莱奥帕尔迪表面支持她的独立,实则利用她的软弱,与玛丽亚暗中勾结,企图控制其财产。
女儿的反抗:阿黛拉的女儿索菲亚因目睹母亲被操控,选择离家出走并公开揭露家庭秘密,成为母女关系破裂的导火索。
代际创伤的循环
玛丽亚的极端控制欲源于她自身的童年创伤——被独裁父亲规训成“完美妻子”。阿黛拉在压抑中重复母亲的行为模式,对索菲亚实施情感绑架,最终在索菲亚的“我宁愿死也不活在你的阴影里”宣言中崩溃。
叙事特色:
多重视角:交替以阿黛拉、玛丽亚、索菲亚的日记片段呈现,揭露家庭秘密的多面性。
意象隐喻:母亲的金十字架项链(宗教规训)、阿黛拉的失眠(精神囚笼)、索菲亚的纹身(身体反抗)贯穿全篇。
烦人的爱主要讲述了中年女性阿黛拉与母亲玛丽亚的纠葛展开。玛丽亚以“为你好”之名,控制阿黛拉的婚姻、事业乃至生育选择,甚至偷看女儿日记,干涉其同性恋情。阿黛拉表面顺从,内心却因压抑滋生出扭曲的恨意。 三角关系的崩塌 情人的背叛:阿黛拉的伴侣莱奥帕尔迪表面支持她的独立,实则利用她的软弱,...(展开全部)
作者简介
埃莱娜•费兰特是一个笔名,作者真实身份至今是谜。埃莱娜•费兰特199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烦人的爱》,1995年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•马尔托内改编为同名电影;此后相继出版小说《被遗弃的日子》(2002),与书信访谈合集《碎片》(2003,2016),小说《暗处的女儿》(2006)以及儿童小说《夜晚的海滩》(2007)。
2011年至2014年,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和《失踪的孩子》,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。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,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友谊,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。
2015年,费兰特被《金融时报》评为“年度女性”。2016年,《时代》周刊将埃莱娜•费兰特选入“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”。2017年3月,《我的天才女友》被改编成话剧在伦敦上演。2017年,HBO宣布将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改编成系列电视剧。
译者简介:
陈英,意大利语言学博士,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,译有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以及《碎片》《愤怒的城堡》《一个人消失在世上》《迫害》《拳头》《威尼斯是一条鱼》《鞋带》《微型世界》等。
目录
版权信息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关于作者
(展开全部)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关于作者
经典金句(30)
纠错 补充反馈
“爱不是枷锁,但你的爱让我觉得自己是犯人。”(阿黛拉对玛丽亚)
意义:
情感暴力批判:将“爱”异化为控制工具,揭露传统家庭伦理中的权力不对等。
存在主义困境:个体在“被爱”名义下丧失主体性,呼应萨特“他人即地狱”的哲学命题。
“我为你牺牲了一切,你却连呼吸都让我窒息。”(玛丽亚独白)
意义:
母职异化: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在子女身上,映射父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训。
代际传递:玛丽亚的牺牲成为阿黛拉的心理创伤源,形成“受虐-施虐”的恶性循环。
“自由不是选择,而是必须承受的代价。”(索菲亚对阿黛拉)
意义:
觉醒宣言:打破“孝道”道德绑架,强调个体自由需以对抗传统为代价。
存在主义行动:索菲亚的出走是对阿黛拉精神殖民的反抗,象征第三代女性的觉醒。
“你恨我,是因为你害怕我比你更自由。”(莱奥帕尔迪揭露真相)
意义:
权力解构: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本质是恐惧——对失去权威的恐惧。
性别政治:男性作为“共谋者”协助女性家长实施压迫,揭露异性恋父权制的合谋性。
“我们不是相爱,是在互相投毒。”(阿黛拉最终独白)
意义:
关系本质祛魅:颠覆浪漫爱叙事,将家庭关系还原为权力博弈的毒性场域。
救赎悖论:承认伤害无法逆转,暗示代际创伤的不可解性。
“爱,是深沉如海的情感,有时却让人透不过气。”
这句话揭示了母女间过度紧密的情感带来的窒息感,呼应了黛莉亚对母亲矛盾的爱与占有欲。
“阿玛利娅就在我的皮肤下面,就像不知何时注入的温暖液体。”
这句话象征着黛莉亚对母亲身份的接纳与融合,体现了自我与母亲角色的界限消解。
“消失的母亲、女儿的原罪和家庭内部的至深之爱。”
这是小说的主题词,直接点明了母女关系中的缺失、愧疚与复杂情感联结。
“爱得太满,像潮水般汹涌,有时也会让人想逃。”
这句话反映了黛莉亚对母亲过度依赖与控制欲的矛盾心理。
“母亲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,她很爱,出于天性、发自肺腑的爱,哪怕离得很远也和自己的孩子连在一起,但她也是自己,一个个体。”
这句话强调了母亲身份的多元性,打破了“完美母亲”的神话,也适用于《烦人的爱》中黛莉亚对母亲复杂情感的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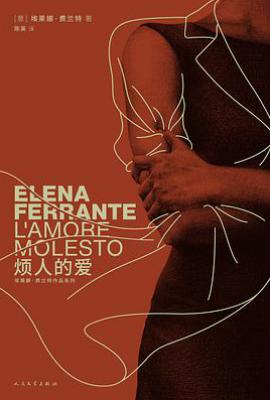
《烦人的爱》不仅是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心理小说,更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、家庭暴力与身份认同的深刻作品。它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主题,引发了读者对母女关系、家庭暴力以及性别压迫等问题的深刻思考。
展开全部当阿黛拉在暴雨中撕碎母亲的金十字架时,《烦人的爱》完成了对家庭伦理的终极审判。它不仅是母女关系的解剖实录,更是一面棱镜——折射出权力规训的隐蔽性、自由意志的暴力性,以及代际创伤的永恒轮回。正如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:铁丝网(控制的具象)、失眠(自由的代价)、纹身(身体的宣言),这些符号共同编织成一部献给所有“在爱中窒息者”的血色启示录。
展开全部